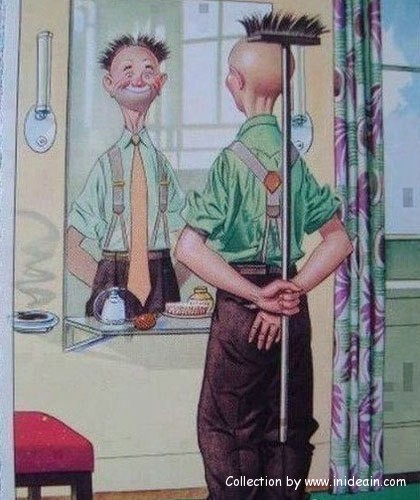我们和自己的父母之间有多大的隔阂?又或有多亲密,能了解他们多少?当我们长大并离家自立的后,父母渐渐老去而我们不在身边,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经历?其实,错过的就永远不会重来,我可以想象得到。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一样。至少,父母健在的时候,我们还是有一种可依靠的归宿感,当他们永远离开时,我们才真正长大。
›文 张晓风
家人至亲,我们自以为极亲极爱了解的,其实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肤表的事件而不是刻骨的感觉。
父亲的追思会上,我问弟弟:
“追诉平生,就由你来吧,你是儿子。”
弟弟沉吟了一下,说:
“我可以,不过我觉得你知道的事情更多些,有些事情,我们小的没赶上。”
然而,我真的知道父亲吗?我们曾认识过父亲吗?我愕然不知怎么回答。
“小的时候,家里穷,除了过年,平时都没有肉吃,如果有客人来,就去熟肉铺子切一点肉,偶尔有个挑担子卖花生米小鱼的人经过,我们小孩子就跟着那个人走。没的吃,看看也是好的,我们就这样跟着跟着,一直走,都走到隔壁庄子去了,就是舍不得回头。”
那是我所知道的,他最早的童年故事。我有时忍不住,想掏把钱塞给那九十年前的馋嘴小男孩,想买一把花生米小鱼填填他的嘴……
我问我自己,你真的了解那小男孩吗?还是你只不过在听故事?如果你不曾穷过饿过,那小男孩巴巴的眼神你又怎么读得懂呢?
读完徐州城里的第七师范的附小,他打算读第七师范,家人带他去见一位堂叔,目的是借钱。
堂叔站起身来,从一把就铜壶里掏出二十一块银元。
堂叔的那二十一块银元改变了父亲的一生。
我很想追上前去看一看那堂叔看着他的怜爱的眼神。他必是族人中最聪明的孩子,堂叔才慨然答应借钱的吧!听说小学时代,他每天上学都不从市内走路,嫌人车杂沓。他宁可绕着古城周围的城墙走,他一面走,一面大声背书。那意气飞扬的男孩,天下好像没有可以难倒他的事。
然而,我真认识那孩子吗?那个捧着二十一块银元来向这个世界打天下的孩子。我平生读书不过只求缘尽兴而已,我大概不能懂得那一心苦读求上进的人,那孩子,我不能算是深识他。
“台湾出的东西,就是没老家的好!”父亲总爱这么感叹。
我有点反感,他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老家的东西比这里好呢?他离开老家都已经这么多年了。
“老家没有的就不说了,咱说有的,譬如这香椿。”他指着院子里的香椿树,台湾的,“长这么细细小小一株。在我们老家,那可是和榕树一样的大树咧!而且台湾是热带,一年到头都能长新芽,那芽也就不嫩了。在我们老家,中有春天才冒得出新芽来,忽然一下,所有的嫩芽全冒出来了,又厚又多汁,大人小孩全来采呀,采下来用盐一揉,放在格架上晾,那架子上腌出来的卤汁就呼噜——呼噜——地一直流,下面就用盆接着,那卤汁下起面来,那个香呀——”
我吃过韩国进口的盐腌香椿芽,从它的形貌看来,揣想它未腌之前一定也极肥厚,故乡的香椿芽想来也是如此。但父亲形容香椿在腌制的过程中竟会“呼噜——呼噜——”流汁,我被他言语中的象声词所惊动,那香椿树竟在我心里成为一座地标,我每次都循着那株香椿树去寻找父亲的故乡。
但我真的明白那棵树吗?
父亲晚年,我推轮椅带他上南京中山陵,只因他曾跟我说过:“总理下葬的时候,我是军校学生,上面在我们中间选了些人去抬棺材,我被选上了……”
他对总理一心崇敬——这一点,恐怕我也无法十分了然。我当然也同意孙中山是可敬佩的,但恐怕未必那么百分之百的心悦诚服。
“我们,那个时候……读了总理的书……觉得他讲的才是真有道理……”
能有一人令你死心塌地,生死追随,父亲应该是幸福的——而这种幸福,我并不能体会。
年轻时的父亲,又一次去打猎。一枪射出,一只小鸟应声而落,他捡起一看,小鸟已肚破肠流,他手里提着那温暖的肉体,看着那腹腔之内一一俱全的五脏,忽然决定终其一生不再射猎。
父亲在同事间并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,听母亲说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“杠子手”,意思是耿直不圆转,他听了也不气,只笑笑说“山难改,性难移”,从来不屑于改正。然而在那个清晨,在树林里,对一只小鸟,他却生慈柔之心,誓言从此不射猎。
父亲的性格如铁如砧,却也如风如水——我何尝真正了解过他?
《红楼梦》第一百二十回,贾政眼看着光头赤脚身披红斗篷的宝玉向他拜了四拜,转身而去,消失在茫茫雪原里,说:
“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,如今叫我才明白——”
贾府上下数百人,谁又曾明白宝玉呢?家人之间,亦未必真能互相解读吧?
我于我父亲,想来也是如此无知无识。他的悲喜、他的起落、他的得意与哀伤、他的憾恨与自足,我哪能都能一一探知、一一感同身受呢?
蒲公英的散蓬能叙述花托吗?
不,它只知道自己在一阵风后身不由己地和花托相失相散了,它只记得叶嫩花初之际,被轻轻托住的安全的感觉。它只知道,后来,就一切都散了,胜利的也许是生命本身,草原上的某处,会有新的蒲公英冒出来。
我终于明白,我还是不能明白父亲。至亲如父女,也只能如此。
我觉得痛,却亦转觉释然,为我本来就无能认识的生命,为我本来就无能认识的死亡,以及不曾真正认识的父亲。原来没有谁可以彻骨认识谁,原来,我也只是如此无知无识。
张晓风的小说创作虽不很多,亦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出版有小说集有《哭墙》、《晓风小说集》等,其中《白手帕》、《红手帕》、《梅兰 竹菊》、《潘渡娜》比较为人所乐道。 《张晓风的国学讲坛》
其中,1968年发表于《中国时报》的《潘渡娜》是台湾科幻界公认的第一篇华文科幻小说,虽是创始之作,在科幻本身的特色方面挖掘得不够深入,但文笔优美、哀婉动人,是当代台湾文坛不可多得的小说佳作。